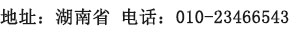史济医院中医科的创始人、首任科主任,从事临床医疗工作60余年。她的那句“他们是病人,是需要救助的对象”,伴随我走过了25年的行医生涯,并指引我在这条救死扶伤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记得那是我刚上班不久,科里安排我跟随史济招教授出门诊。患者很多,都快中午11点了,可史教授看了还不到一半的患者。排在后面的患者不耐烦了,不时推门询问“看到几号了”。那时候,没有电子叫号系统,更没有大屏幕显示患者排队顺序,患者将挂号单据连同病历手册交到诊室,然后在外面排队候诊。为了让专家教授专心诊病,回答患者询问的任务自然就由我们年轻医生承担起来。
等候的患者及家属越来越不耐烦,询问的次数不断增加,起初还能心平气和回答询问的我,情绪逐渐被搞得“乱七八糟”。当史教授诊完一个患者,开门的瞬间,蜂拥而上的患者及家属七嘴八舌地问“是不是该我们了?”就在这时候,人群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高音喇叭”,声音中夹杂着急躁,“怎么还没到我们,都快中午了,还差几个?”
“叫什么名字?”我一边问,一边匆匆翻看排队的病历手册,“下一个是您”。那人似乎又嘟囔了几句,我没再理会,关上门,诊室安静了许多。等史教授让我叫下一个患者的时候我才发现,刚才那个患者前面还有一个病历手册,但因完全被压在下面,加上我心绪烦乱,翻看不仔细,没有看到。
开门时,我只能按顺序叫排在前面的那个患者。当听到我呼叫的名字不是他时,那人突然冲出人群(后来知道是患者的家属),揪住我的衣领,喘着粗气吼道:“我算明白了,这一上午我们等这么长时间,都是你小子搞的鬼!你是不是找揍呐?”我还来不及做出其他反应,那人不容分说,一边吼叫,一边将我拖出了诊室。虽然在史教授、科主任和几名闻讯赶来的医生的劝解下,我最终脱离了“危险”,但那人始终咬牙切齿,认定是我搞的鬼。在他的家人看完病要离开时,他还一脸凶相地用手指着我威胁道,“下班后当心点儿!”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闷闷不乐,甚至一度产生了职业倦怠情绪。倒不是因为担心当事人要找我算账,而是觉得自己作为医生完全不被患方理解,甚至被误解,因而想不通。
史教授察觉到了我的心思,在一次门诊结束后,讲述了她自己的一个故事来开导我。
曾经有一位肝硬化的患者,医院“判了死刑”,后来找到史教授寻求中西医结合治疗。“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能挽救他的生命。”史教授眼眶湿润,声音哽咽,“可是最让人气愤的是,他的家属却认为是我治死了病人。”后来,患者家属反复找史教授的麻烦,还不停地打电话辱骂史教授。这种情况持续了近半年。“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很气愤。可他们是病人呀,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患者家属失去了亲人,我们也应该理解他们的痛苦。慢慢地,我也就原谅了他们。你刚刚上班,以后还会遇到很多事情,对待患者一定要记住:他们是病人,是需要救助的对象。”史教授感慨道。
“他们是病人,是需要救助的对象。”一句话,看似普通,却催人深省。遇到不被理解的时候,自己为什么不能换个角度来思考,体谅一下他们的心情?其实,仔细想想,此事的发生,自己的做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我能在他们询问排队顺序的时候不急不躁,能够仔细查看病历,准确报告顺序,或许后面的事情不会发生。说到底还是自己“修炼”得不够!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在所著的《大医精诚》中就讲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我连“安神定志”都未做到,更何谈“无欲无求”?想到这些,心中的迷雾慢慢散去,在工作中逐渐找回了自信,日后处理此类事情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大概是一年以后,轮转到病房的我收治了一名急性胰腺炎的患者,治疗措施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禁食禁水”。但患者的母亲大为不解,厉声质问:“人是铁饭是钢,现在你们不让我儿子吃饭,想饿死我儿子吗?你们是什么医生?”这次,我平静了许多。虽然多次心平气和的解释始终无果,我仍旧不急不恼,排除杂念,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精心救治。看到她儿子的病情一天天地好转,逐渐恢复了饮食,这位母亲的脸上最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出院时还特地找到我表达了感激之情,对于之前她不理解医生的言行也表示了歉意!
是的,既然我们选择了医生这一高尚的职业,就应该时刻牢记“他们是病人,是需要救助的对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时刻把救助病患疾苦当做自己的第一要务,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承担一切。即便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被冤枉,也能始终以宽厚仁爱之心,对待患者及家属。(文/医院中医科田国庆)
编辑制作:朱永基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