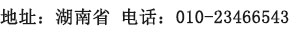片警微述评Ⅱ:适当放缓一些试验,让落后的灵魂赶上来
在抗HBV新药研发中,CpAMs可能是走得更快的,进入各期临床试验的抗HBV新药也多是该类药物。目前,CpAMs的临床试验多与NAs联合使用。但从已有的临床试验结果看,联合CpAMs并未显著加速NAs治疗下的cccDNA耗竭或静默,以至于在几项有限疗程的联合治疗后,几乎所有患者都发生了病毒学反弹。我们知道,CpAMs主要通过干扰core蛋白包裹pgRNA/P蛋白复合物组装成核衣壳的过程,使逆转录过程失去了适宜的反应场所。而NAs通过竞争结合P蛋白。抑制的恰恰就是在核衣壳内发生的逆转录过程。不难想象,联合用药下的NAs难再成为抗病毒的主力,发挥的可能仅仅是堵漏的作用。此情此境下,我们或许就不能期待两强联合会出现“1+1=2”的叠加效能了。除此之外,我们应该能够想象的到,核衣壳内的pgRNA不会是以无序状态自由悬浮其中,更像是以适当的方式“悬挂”在填充着dNTP和一些未知宿主蛋白的衣壳腔内。生信分析的结果提示,pgRNA或许真实存在能够与构成衣壳的core蛋白结合的基序。CpAMs影响下的核衣壳可能真就失去了其正常的结构和壳内空间,如此一来,pgRNA/P蛋白复合物的蛋白质priming是否能够起始?首次跳转是否进行以确保逆转录能够正常启动?此情此境下NAs是否还能发挥对逆转录过程的竞争抑制作用?目前并无确切的答案。若果真如此,CpAMs联合NAs的叠加抗病毒作用是否更容易碰到药物效应的玻璃天花板?期许两强联合加速cccDNA池耗竭的作用会不会难以成真?事实上,从文献报道的一些CpAMs联合NAs的临床试验研究结果看,患者血清HBsAg或HBcrAg在短期治疗后的确无明显的下降,也许说明了这一点?总之,现阶段CpAMs的联合治疗之路步履蹒跚,可能需要我们缓下步伐,等一等落后的灵魂。在未来的以安全停药为观察终点的临床试验中,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CpAMs和NAs联合治疗以耗竭或静默cccDNA池,以提高停药安全性。三
新型药物:直接抗病毒药物
1、靶向病毒药物
(1)抑制病毒复制
进入抑制剂布列韦肽(BLV)为肉豆蔻酰化多肽,带有L-HBsAg的PreS1区序列,能够结合NTCP以阻止HBV和HDV进入细胞。在已开展的临床试验中,BLV对于HDV有较好的疗效,已被欧盟有条件地批准用于治疗慢性HDV感染,FDA也已授予该药物“突破性疗法”地位。但是,其对于CHB患者的疗效仍然有待确定。
衣壳组装调节药物(CpAMs)可分为两种作用类别:I型CpAMs干扰核衣壳正常组装使之形成多种形态的非衣壳结构;II型CpAMs则通过促进结构“正常”但无pgRNA/P蛋白复合物的空衣壳形成。CpAMs的上述作用干扰了核衣壳正常组装或增加空衣壳组装,从而抑制pgRNA包装。此外,CpAMs还有增强成熟核衣壳的非正常解聚和干扰rcDNA正确释放入核回补cccDNA的过程。并且,CpAMs对所有HBV基因型均具有抗病毒活性,且由于与NAs耐药突变不重叠,预计CpAMs对NAs耐药变异株也会有作用。与应用ETV单药治疗相比,CpAMs与ETV联合治疗下HBVDNA和HBVRNA下降幅度更大,且无耐药变异株出现。应用CpAMs治疗时,HBVRNA减少是药物作用于靶点的重要证据(注:但并非代表cccDNA被清除或被静默),在HBsAg或HBcrAg无明显下降的情况下,以“安全停药”为重要观察终点的两项CpAMs临床试验中,几乎所有病人都在停药后发生了反弹。目前,两种CpAMs的研发因为患者出现ALT急性升高而中断。目前,更多强效的CpAMs正在研发过程中。
视黄酸诱导基因I(RIG-I)是一种先天免疫系统中的模式识别受体,可以感知pgRNA并诱导肝脏III型IFN的产生。伊那瑞韦(Inarigivir)是一种二核苷酸药物,能激活RIG-I并且通过结合pgRNA进而抑制逆转录过程。在NAs经治的患者中,Inarigivir能够使超过半数患者(55%)的血清HBsAg水平下降超过1个log10IU/mL。但因为患者用药后会出现多种严重的副作用,包括停药后ALT急性升高、坏死性胰腺炎、药物诱导肝损伤和脂肪变性风险等,其临床实验进展现已停止。
(2)减少病毒抗原
核酸聚合物(NAPs)是一种HBsAg释放抑制剂,能通过抑制HBV亚病毒颗粒的组装及释放,从而使血清HBsAg水平显著下降。其中REP-和REP-在临床试验中表现出了非常高的HBsAg消失率。但其确切的作用机制、长期安全性、应答反应的持久性及免疫重建程度仍不清楚,需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验证。结构上与NAPs类似的s抗原转运抑制寡核苷酸聚合物(STOPS)代表了另一类HBsAg释放抑制剂,在早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小干扰RNA(siRNA)是一种双链RNA,能靶向、结合并沉默HBVmRNA,并借此遏制病毒蛋白质的翻译。设计在不同基因区的siRNA可靶向HBV的不同转录本。此外,siRNA还可通过共价结合N-乙酰半乳糖胺从而促进其被肝细胞所摄取。但由于siRNA一般采用静脉或皮下注射,故有引发过敏反应的风险。siRNA单一用药或联合NAs用药2-4个月,可使患者血清HBsAg水平下降约2log10IU/mL。而与siRNA单药相比,siRNA、NAs及PEG-IFN三药联用可使HBsAg更显著的下降(3log10IU/mL)。
反义寡核苷酸(ASOs)为具有核酸酶抗性的单链短核苷酸,在高浓度下能够进入肝细胞。其作用与siRNA相似,能够抑制病毒蛋白翻译,且能减少病毒颗粒和亚病毒颗粒的分泌,但治疗后HBsAg转阴并不持久。
还有一类是能够直接靶向抑制病毒rcDNA向cccDNA的转化、并对cccDNA进行靶向清除或表观遗传沉默的在研药物。例如,锌指核酶(ZFN)能直接切断cccDNA中的特定序列;转录激活因子样效应物核酸酶(TALEN)能编辑HBV基因或表观遗传学上修饰,从而沉默HBV基因;引导RNA(gRNA)介导的Cas9能够直接切断cccDNA,但因脱靶效应有造成宿主基因组断裂之虞。虽然这些药物在临床前研究中都有不错表现,但至今没有应用于患者治疗。
图1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简要机制
四
新型药物:免疫调节剂
1.先天免疫调节剂
先天免疫调节剂可分为Toll样受体(TLR)激动剂和RIG-I激动剂。区分其类型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模式识别受体的分布,TLR主要在特定的细胞上表达,而RIG-I的表达更为广泛。靶向TLR的药物主要诱导抗病毒和炎性因子生成,也能诱导细胞因子生成。TLR-7激动剂维索莫德(GS-)、TLR-8激动剂塞尔甘多莫德(GS-)及RIG-I激动剂Inarigivir均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出极高的抗病毒效力,并且不会受血浆中的病毒或抗原载量影响。临床试验显示,GS-或GS-分别和NAs药物联合使用时非常安全,但这些药物在CHB患者中并没有表现出其在动物模型中所展现的抗病毒效力。
2.治疗性疫苗
获得性免疫在急性HBV感染消退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而增强获得性免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治疗性疫苗,然而目前最明显的障碍是对患者循环中的病毒抗原水平进行定量。CHB患者体内血浆中HBsAg水平为IU/mL(相当于~25μg/mL)时,按总血容量为mL可换算成HBsAg载量为68mg。因此,治疗性疫苗所递送的HBV抗原与天然循环中可引起足够免疫识别的抗原水平有很大差异,这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有效诱导CD8+T细胞免疫,人们着重开发了基于病毒载体的治疗性疫苗。病毒载体能够“感染”注射部位的细胞并在细胞质内表达疫苗抗原,将HBV抗原呈递给MHC-I和MHC-II分子、激活CD8+和CD4+T细胞,并协调Th1细胞分泌细胞因子。腺病毒载体在人体内有高度免疫原性,能够在健康的供体或在T细胞耗尽状态的慢性丙肝病人中,诱导强有力的T细胞和B细胞免疫反应。在未来研究中,新型疫苗很可能与减少HBV复制的直接抗病毒药物联合运用,以显著增加HBV特异性T细胞和B细胞反应。
3.检查点抑制剂
检查点抑制剂通过遏制相关免疫抑制信号通路来增强宿主对HBV的特异性免疫,主要是细胞程序性死亡蛋白-1或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D-1或PD-L1)通路。目前,此类药物在非HCC的CHB患中的相关数据有限,仅有一项I期临床试验显示出nivolumab与治疗性疫苗联用的安全性。除治疗性抗体外,还有其他可干扰抑制该通路的方法,如使一些半衰期短的小分子结合PD-L1并使之内化,或通过递送靶向PD-L1的ASOs来降解肝细胞内PD-L1转录本从而抑制其表达。但是并不是所有病人都对检查点阻滞有反应,靶向PD-1/PD-L1的药物特异性仍待研究。
4.抗HBs
抗-HBs单克隆抗体能够降低循环中的HBsAg,并可作为进入抑制剂来阻止HBV进入肝细胞,还能够制造免疫复合物加快将抗原输送给专业的抗原呈递细胞,以此增强T细胞的免疫反应。但这可能需要频繁给药以维持HBsAg抑制状态。用治疗性疫苗将抗原从循环中清除可以增强外周T细胞反应。抗-HBs单克隆抗体有作为联合治疗方案用药的潜能,但这仍需要后续临床试验来证实。
图2各免疫调节剂简要作用机制
总结
抗HBV新型药物的研发及临床试验的进展为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治愈带来了希望。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的药物难以直接清除cccDNA及整合的HBVDNA,未来的药物研发需要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