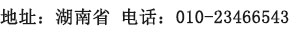流苏花开
张克奇
在我心里,一直有两棵流苏树在盛开着。那些流苏花边一样密密匝匝的白色小花,挂满每一根枝丫,犹如无数片雪花把四月里正浓的春光又顽皮地挑逗了一下。
那树,就静静地生长在山东省临朐县柳山镇庙山村村西的那片沃土上。它们原本是明代乡村眼疾名医张化露栽植在花盆里的心爱之物,张去世后,子女们出于孝心,便将其移栽于他的坟前,让它们日夜陪伴着父亲,以化解老主人的孤独和寂寥。根植于那片肥沃的土地,流苏树饮风沐雨,茁壮成长,逐渐从盆栽之物变化为挺立于天地之间的大树。它们的头冠,也日益铺张蔓延开来,状如华盖。
六百五十多年的光阴荏苒里,没有人能清楚地洞悉它们身上所有的故事,也无从猜想它们究竟躲过了多少的天灾和人祸。历史所能清晰地记下的一个是,它们原本三胞胎,其中的一棵在年被日伪汉奸伐去盖了炮楼。听老人们讲,若不是村民们齐心协力以死对抗,一棵也不会留下。对于岁月和那些上了年岁的事物,我一直心存敬畏。凡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存下来的,不管是一棵树,还是一座桥,亦或是一座简陋的建筑、一块简朴的碑碣,都附存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密语。透过或循着这些密语,人们才能拨开历史的烟云找到回家的路。
柳山,一个多么诗意的名字。一想到那么多柔软的柳条随风而舞,犹如数不清的美发在长飘,人心就禁不住荡漾了。因为土地平坦肥沃,这里早在春秋时代就建起了城池。临朐旧志记载:西汉时曾在此设立朱虚侯国。位于柳山镇孟津河西岸的魏家庄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一处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古文化遗址,曾出土石铲、石斧、石刀、石镞和红陶、黑陶鼎、罐以及象征权势和地位的蛋壳陶高柄杯残片,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汉代的庙山遗址,也被列入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庙山在明朝由张氏立村。这支张氏在临朐的始祖于元末自河间府(现在的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斑鸠店庄逃难而来,初居双山之阳,再居高家庄,其后一子东迁汶河之西白塔之北锹土诛茅,以就口食。由于居无定所,他们只好砍伐一些树枝搭成简易的窝棚遮风雨避寒暑,故称“窝铺”村。永乐年间,五世祖张鹏又从窝铺迁到庙山,因村东南麓有苗山子,村名就叫做了“苗山”。明朝万历年间,村西建起关帝庙,供奉关公、关平、周仓神像,村名遂改称“庙山”。窝铺张氏的文化基因非常强大,虽没出过彪炳史册的大人物,算不上是名门望族,却也有文进士张初旭,文举张柱、张敦仁,武举张居常,著有潍坊地区首部聊斋志异体小说《筒丸录》的张新修等一批先贤名流支撑着门面。我之所以对此这么了解,是因为我和庙山族人同宗同祖。
庙山张氏后裔一脉相传,崇文重教之风盛行,明清时代即设有私塾,民国时期设立初级小学。村人自古多才多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就成立了剧团,吹拉弹唱各样人才俱全,是远近闻名的文化村。如今村里的书画协会、秧歌队、吕剧团等队伍更是蓬勃发展,还出现了张森顺、张敬源等一批书画名家和文化带头人,文艺活动常年不断,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庙山人不仅有着深沉的崇文情愫,还有着极为浓厚的尚武情结,形成了崇文尚武的底蕴和特色。“武”为抵功拳,其祖师是有着“神拳”之称的安丘人张璀。张璀因母患眼疾慕名到庙山就医,张化露知道张璀武术精湛,求其教授拳艺。从此,张璀的抵攻拳就在庙山流传下来,目前已经传至第六代,成为非遗项目。
仔细深究,庙山的文武之道,均以“孝”为核心。张化露的子女将父亲生前爱物移至父亲坟前,是一种大孝;张璀为给母治疗眼疾,不惜将家传的抵攻拳法倾囊相授,也是一种大孝。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的两棵流苏树,默默地见证着这一切,也见证了一代代庙山人自强不息、薪火相传的创业历程。为了充分发挥两棵流苏树的品牌效应,庙山村从年开始以其为载体,积极联合县镇两级举办流苏文化艺术节,不仅大力传承弘扬了“孝文化”,还很好地实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双赢、多赢。
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近年来庙山村大力发展大棚西瓜、有机蔬菜、流苏苗木培育等产业,并将农业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积极发展生态休闲农业、农业观光、休闲采摘等项目,努力拓展发展链条。这一套完美的“组合拳”打下来,群众的腰包鼓了,村集体的收入也增加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服务都得到了很大改善,老百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你若有时间走进庙山,会发现每家每户都种养着不少花草,有些品种还非常娇贵,颇显富足后的闲情逸致。因为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发展新路子,这个曾经的“省定贫困村”也迅速蝶变为潍坊市“市级美丽乡村”、首批“山东省十百千乡村振兴示范村”。今年春节期间,作为县派庙山村的第一书记,我亲眼见证了村里第一茬大棚西瓜上市的情景:15元1斤还供不应求,并且根本不用出去卖,光春节期间串门走亲戚、自动找上门来的顾客就给“包了圆”。一通紧张的忙碌之后,村党支部书记张传礼扳着手指头给我算了一笔账:这茬西瓜能采摘到2月下旬,我这个二亩半的大棚预计毛收入十五六万,除去人工、肥料等成本,还能剩下八九万元。说到这里他把头一仰,满脸阳光地说:村里家家户户年年都是个忙年、累年,但年年也是个富裕年啊!
从大棚西瓜种植园里出来,我又来到了宽阔的流苏文化广场。仰望着眼前两棵高达20多米的流苏树,觉得它们既像兄弟、姊妹,也像一对夫妻一样,相互偎依,相互扶持,一起走过生命的风风雨雨。就像村民们抱团合作,互帮互助,共同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古树前久久伫立,我还不禁想起了几件事:一个是村里的一位老人给我讲的,他说年秋的一天,一场山火借着风势无情地向村里袭来,几乎是一瞬间就将流苏树东边相距不远的4间民房烧毁,2间烤烟房也被烧塌了架,可是当大火眼看就要烧向流苏树时,突然天降大雨,将熊熊大火迅速熄灭,两株流苏树完好无损,就连堆放在树下的柴火堆都没有点着。村民见此情景不禁诧异万分,都说古树有灵。第二个是书籍上记载的:明万历四十三年(年)春,天气久旱无雨,老百姓生活用水都非常困难,甚至舍不得用水洗手洗脸,可即使缺水缺到这样的程度,每家每户仍然每隔几天就自觉留出一碗水,轮流去浇那两棵流苏树,终于使古树顺利度过旱灾。还有一个也是书上所记:清咸丰七年(年)发生严重蝗灾,蝗虫所到之处,草木树叶皆被啃食一空。为使流苏古树不受蝗虫袭扰,村民轮流值班,烟熏火燎驱赶蝗虫,帮助古树再逃一劫。这几件事,第一个也许有些灵异,后面两个和前面说到的村民面对凶恶的日伪军冒死护树之事,却很好地诠释了事在人为的道理,也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对这两棵流苏古树的深厚感情和敬畏之心。老百姓的心就是这样朴素,也是这样明澈。
当下时节,两棵流苏古树又如约盛开。五一这天,我约上家人再次来到庙山,眼前两个巨大的树冠洁白如雪,纤尘不染,幽幽花香,若有若无。尽管有着严格的疫情防控,可慕名前来参观的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古树身上的传奇故事、所承载的孝道文化也在大家的口口相传中得到了深厚绵长的传颂和升华。这次我妻子还有一个新发现:从西南方向往东北看去,西边那棵流苏两条粗壮的树枝竟然在空中完美地呈现出了一个“心”的形状,立即就让人想到了心心相印、同心同德等美好的寓意。千年流苏芳菲绽,最美人间“四月雪”。这每年一场的浩大而安静的盛开啊,多像对苍茫历史的一种缅怀,又多像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新征程的深情礼赞!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